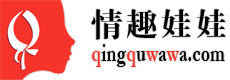“换偶游戏”近年来在美国中产阶级间大行其道,据统计,目前全美已有超过500个"换偶俱乐部",有些大型的换妻俱乐部甚至会包下一整座大饭店,让多达4000人举行热情如火的换妻派对。
洛杉矶换偶俱乐部负责人拉齐莱特表示,上个世纪70年代从事换妻游戏的人大多是个性叛逆、长发披肩的嬉皮夫妻,而今换偶人士多为30岁至40岁、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中产阶级夫妇。每逢周末,从加州圣荷塞至旧金山等大城市都会举行交换性伴侣的换偶派对。
“换偶”为避免婚外情?在欧美换偶不是新鲜事,尽管大部分人觉得这种行为非常荒唐,但参与其中的人却自有一套说词,他们认为夫妻相处久了,难免厌倦对方,为避免发生婚外情,不如在彼此谅解的情况下,透过换妻方式“疏解”一下。
参与换偶活动的人多自认“思想开通”,他们坚信人性软弱,与其逃避现实、苦苦压抑,不如和其他想法一样的夫妇进行交换计划。
徐:这是前不久在中国各大媒体上刊登最多的一则新闻,实际上看来它早就是旧闻了,因
洛杉矶换偶俱乐部负责人拉齐莱特表示,上个世纪70年代从事换妻游戏的人大多是个性叛逆、长发披肩的嬉皮夫妻,而今换偶人士多为30岁至40岁、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中产阶级夫妇。每逢周末,从加州圣荷塞至旧金山等大城市都会举行交换性伴侣的换偶派对。
“换偶”为避免婚外情?在欧美换偶不是新鲜事,尽管大部分人觉得这种行为非常荒唐,但参与其中的人却自有一套说词,他们认为夫妻相处久了,难免厌倦对方,为避免发生婚外情,不如在彼此谅解的情况下,透过换妻方式“疏解”一下。
参与换偶活动的人多自认“思想开通”,他们坚信人性软弱,与其逃避现实、苦苦压抑,不如和其他想法一样的夫妇进行交换计划。
徐:这是前不久在中国各大媒体上刊登最多的一则新闻,实际上看来它早就是旧闻了,因为它产生于美国70年代的“性革命”,现在只不过是余波而已。一提起美国,我们对它的感觉便是自由,尤其是性自由。从那些四海同时播放的好莱坞影片中,我们总是能得出一个结论:漂亮的女主人公在认识一个同样性感的男人五分钟后,就可以上床;而且他们的性欲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强,他们的性伴侣难以计数,他们的孩子很早时就在学校里发生无数的性行为,他们的家庭总是被性困扰着,等等,总之,给我们这个传统保守的民族一个深刻的印象,美国就是一个放纵的民族。他们的生活被我们说成是腐朽的,他们的行为是自由化,我们总是在内心深处一边接纳它,又一边提防着它,生怕它那床上的功夫毒害了我们的民族。现在看起来,它一方面可能是宣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有历史原因的,也就是说,美国人有着“性革命”的历史。也许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就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东西。从上面这个旧闻中,我们就可以窥见美国人的“性革命”是怎么回事了。
刘:“性革命”是在美国发生,但它迅速在整个西方社会流行。中国人对它的了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那时已经到了“性革命”的尾声。“性革命”爆发于60年代的西方社会,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人们对它的评价,一直是褒贬不一。王溢嘉在《性·文明与荒谬》一书里对它进行了一番折中的总结:“它‘复古’的成分可能要大于‘革新’,从历史与进化的宏观格局来看,‘穿衣服’与‘禁欲’才是‘革命’,‘脱衣服’与‘纵欲’实在是‘复古’。从观念与行为的认知结构来看,‘性革命’的内涵都是早就‘存在’于个人隐密而恣纵的性幻想中,或者其他文化、其他阶级的日常生活之中,它的现身只是一种公开而普遍的‘实践’”
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从“性革命”对维多利亚时代禁欲主义的彻底扫荡来看,这也可以算是一场革命;如果从“性革命”以后脱轨,走向裸体、纵欲、滥交来看,这的确是“复古”到野蛮时代去了,那不是革命,是倒退。不过,无论怎么说,“性革命”总是人类性发展史中否定之否定的长链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还是值得分析的。
徐:正如上面消息中所说的,“性革命”时代,参加这一运动的大都是些个性反叛的青年,而且他们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出身也比较富有。可能就像现在我们国家出现的“七十后”这一代吧,他们自称为小资。那时,美国的青年主要干了些什么?
刘:由于他们不满足于传统的小家庭生活方式,反对对性的压抑和禁锢,对传统的两性关系形式表示了极大的反抗。他们单纯强调要尽情地享受性的快乐,过早地发生婚前性行为,甚至公开同居,视结合与离异为儿戏。有些青年还聚居在一起,组成“大家庭”,过群婚乱交的生活;此外还出现了许多婚姻形式,如同性恋婚姻、合同婚姻、临时婚姻、家庭群等。
徐:您前面说过,这是历史否定之否定中的一链,也就是“性革命”在您看来有着历史渊源。
刘:是的,它不是偶然产物,而是一种必然。这得上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那种肯定现世人生、追求人世欢乐的思想:提倡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而这些思想一旦和性联系起来,就成了对“性自由”的追求。
但是欧洲清教运动的兴起和维多利亚主义的广泛流行,使人文主义的光辉暗淡了下来,社会思想又从开放走向了保守和禁锢。到了20世纪,各种思想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发展,重新又唤起了失落的人文主义,因而也唤醒了性。
徐:这应该是思想根源。欧洲文艺复兴如果说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纵欲主义的复兴的话,这次性解放应该走得更远,它试图与原始社会的性达成一致。19世纪末科学主义和进化论、考古学、人类学的兴起,使人类不仅对宗教思想进行了更大的打击与报复,还使人类睁开了眼睛,发现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从亚当和夏娃开始,而要更早,对家庭婚姻制度的研究也使人类对两性关系有了重新认识。这一切使60年代的“性革命”带上了“野蛮”的色彩,实际上这正是人们的学说影响的。如果没有“原始群婚说”,如果没有对偶婚的发现,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不否定一夫一妻制(他们预言一夫一妻制将随国家、法律等的消亡而消亡),那么,那些群婚乱交的行为就不会有理论基础。可以说,“性革命”是这些学说的副产品。
刘:这只是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的,关于性的理论才是“性革命”真正的理论基础。19世纪末兴起了现代性科学,先是弗洛伊德从本能生物学上认为,存在于无意识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是支配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尽管他遭到了很多批评,但人们对性的真正关注和重视,却是从他开始的。后来,霭理士一再地强调:“性是自然而令人喜欢的”,“性欲是卑下邪恶的观念乃是宇宙中的一大荒谬,就好像疯子认为他的食欲是邪恶而拒绝进食一样”。在两位先驱的影响下,后世学者极力地鼓吹性欲应该怎么自由,
这些都从根本上引导了人们的性观念。而40年代和50年代公布的两个金西调查报告对“性革命”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人们读了金西教授的报告后得出一个结论:既然人们的性生活实际上竟是如此,我为什么还要抱着那陈旧的一套不放呢?
徐:我们中国人对性心理学的泰斗弗洛伊德知道的已经很多了,但对另一个泰斗霭理士以及现代性学先驱金西并不了解,请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刘:霭理士是英国的性心理学家、作家、文学评论家,他出生的时候正是维多利亚性保守主义的全盛时期,他本人有着严重的性困扰,深受其害。他当过教师,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并挂牌行过医,但不久就专心于文学写作评论和性研究。他不是从某个学科领域单独地研究性问题,而是从民族学、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诸领域综合论述性的问题。他的著作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性心理学》和《天才与遗传》等。
在谈金西教授之前,我们必须还得说说他前后的几个在人类性学方面有着重要贡献的人。
在历史上最勇敢地站出来进行人体性实验的人是美国科学家华生。因为在此以前,人们对性的认识一直停留在社会科学方面,充满了臆测、迷信和无知,还有恐惧。要真正理解人类的性行为,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性反应的客观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例如男人和女人的性欲究竟是不是相同的,女性性反应高潮是否可以截然分出“阴道高潮”和“阴蒂高潮”,自慰行为究竟对人体有没有害处,等等。在那时,他进行的性反应实验研究,是无人和他合作的,妻子更是持反对态度,他只好偷偷地和女秘书在实验室里进行,积累了大量实验资料,最后却被妻子发现付之一炬,并被法院判决他是“坏行为的专家”。他也被大学辞退,做了一个广告公司的小职员,后半生碌碌无为。但他的心理学专著,至今仍被人学习、引用。
完成华生未竟事业的是四十多年后的玛斯特斯和约翰逊夫妇,这时候,“性革命”已经开始了。在11年中,他们所观察的模拟性交和实际性交实验达1万次,其中男性2500次,女性7500次。他们把大量的实验数据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于1966年出版了第一部专部《人类性反应》,轰动了整个西方社会,成为现代性科学的经典著作。他们的研究,革新了人们对性反应的认识,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具有划时代影响的金西教授的调查。美国人亚弗雷德·金西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26岁就成为印第安那大学生物学教授,在1938年因为这所大学的女联会学生代表要求学校为那些已经订婚、结婚或准备结婚的学生开设有关“人类性学”的课程,他就成了这门课的教师。在他备课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学科缺乏具有科学依据的统计资料,无法回答学生的提问。于是,他放弃了先前对昆虫有研究,开始了有关性的调查。在整整10间,他和他的同事们对17000人进行了调查,于1948年出版了《金西报告》的男性篇《人类男性性行为》,人们终于知道,有90%以上的男性有过自慰的经验,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男性承认从青春期开始至少有过一次与其他男性的性经验。1953年,女性篇《人类女性性行为》出版,人们突然发现,有一半的女子在婚前有过性行为,25%的女性承认自己有婚外性行为。
金西研究的原意是想打破社会上对性行为保持缄默的维多利亚时代式的旧观念,可是他的调查报告一出,随之而来的性行为的自由和性方面的公开讨论与研究就一发不可收拾。那些数据大大动摇了常人的道德观念,突然间,性方面的话题不再限于卖淫、性病、节育和弗洛伊德理论等等,而进入了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同性恋、性变态等过去避而不谈的禁区。这个报告的影响远不至如此,他使美国的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的那一套性的道理规范被认为是虚伪的,站不住脚了。所以完全可以说,金西报告在理论上直接推动了美国60年代开始发生的“性革命”。
西方社会对性学的研究从金西以后就非常热闹了,似乎每10年就出现一两位代表人物:就50年代来说,是金西的调查;就60年代来说,是玛斯特斯和约翰逊;就70年代来说,是莎丽·海特;就80年代来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劳曼、马可和迈克斯等人的调查。
徐:这些调查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在方法论上改变了以往的研究,还给性在统计学上定位了。这种定位究竟有没有道理,我倒总是怀疑,因为不一定人人都这样就这认为这是好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不过,它毕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足以说明它是可以信赖的。
刘:前面所说的只是观念上的原因,在经济、政治方面也有原因。如前面所说,“性革命”的主要参加者大都是中产阶级,他们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而“性”也想当然地成为消费的对象。有的学者还把美国汽车业的迅猛发展也看成“性革命”的推动者,因为它可以在几分钟之内让那些年轻人逃离道德的包围圈,而进入另一个相对陌生、自由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至于政治上的原因,很多学者主要把它归于两次世界大战。许多人庆幸战争的灾难已经过去,生命实在太短暂了,还不如及时行乐的好。
徐:这让我想起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写的那首著名的诗《嚎叫》,和另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等待戈多》、《在路上》,它们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那时的美国青年是何等地空虚、无聊而又绝望,绝望到了要嚎叫。
而这空虚和绝望又使我想起西方一个哲人大叫“人死了”,这是继尼采的“上帝死了”之后对人类价值,准确一些说是人文主义的绝望。他们再也找不到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于是行为主义就成为青年人推崇的重要方式。而行为主义在根本上说,也是无事无补的,因为它无法说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行为本身似乎也死了。这就是说,这个世界死了。这是多么地可怕!由此我想说的是,既然西方世界的精神已经倒了,他们所奉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矛盾与倒退,而我们的青年却还是觉得人家的好,要不顾一切地模仿,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的很多学者,如果一旦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会对人说:“你看看人家西方是怎么怎么地”,西方成了唯一的准则。我希望“性革命”不要也被我们的社会学家和性学家毫无取舍地推行到中国来。
刘:前面我们似乎已经谈过,我觉得中国是不可能爆发“性革命”的,因为我们古老的文化在制约着性。 徐:但愿如此。除了前面说的原因外,还有哪些原因?
刘:妇女解放运动也是“性革命”的兴奋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阶级的融合--人口从乡间涌向城市,人际空间渐趋紧密,职业妇女地位提升,使得传统的父权制逐渐崩溃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男子上了战场,女子取代他们的工作,使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而取得独立。在这种运动中,有不少妇女产生了争取性自由的勇气,妇女在性方面的开放和主动也成为“性革命”的重要内容。
除了这些原因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20世纪性之所以非常开放的重要原因,就是口服药和避孕套的使用。这是科学带来的。科学说,你们大胆地进行性交吧,只要你们不忘记我的发明。人们也这样做了,而且发现它完全实现了另一场革命,那就是生殖与性活动可以分离。
徐:既然人们对“性革命”有褒有贬,也就是说它既有合理发展的一面,又有可恶的一面,那么,如何来认识它呢?也就是说它如何在真理与荒谬间徘徊的?
刘:前面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点,这也是首要的一点,就是性学家对性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对性的神秘感和负罪感,使人类得到了一定的解脱。同时,也使人们开始重视性科学研究和性教育的普及。在这些研究中,除了金西的调查外,尤其要提的是玛斯特斯夫妇的实验,他们的理论可以说奠定了性科学的基础。
徐:我们都知道人类性反应的四周期理论是他们提出来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得出了哪些惊人的结论?
刘:他们第一次指出,男女性反应极其相似,并不是女性比男性迟钝或相差甚大,并纠正了弗洛伊德提出的女子性反应高潮分为“阴道高潮”和“阴蒂高潮”两个阶段并极力贬低“阴蒂高潮”从而引起很多不良后果的错误说法;他们发现男性阴茎的大小与性快感并无必然关联,发现女性的阴蒂和男性的阴茎并非类同的器官,并发现阴道润滑液的产生是性兴奋时阴道壁的一种“发汗”,而不属于腺体分泌物;他们还发现决定男女生理特征的同一性激素并不是其绝对数量,而是其比值;他们纠正了手淫对人身体有害的错误说法,明确了勃起中枢是在脊髓的末端部位,等等。他们的发现对如何促进性健康,保持和谐的夫妻性生活,以及有效地进行性治疗,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创造了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见效而且总疗效在80%以上的各种性功能障碍的新治疗方法。
徐:说到这里,我想起在我刚刚毕业时看过的一本《圣床》,当时被认为是黄色书籍查禁了。
刘:玛斯特斯夫妇对阴萎的治疗提出用“双性疗法”,而且这也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对多数患者是奏效的,但对一些夫妻不怎么合适,特别是有些男子是未婚的,就不可能用夫妻的方法来治疗,所以他们大胆地使用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女性担任“代配偶”进行治疗。但是这一做法与社会道德发生严重的冲突,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卖淫”,所以这种方法到1970年停止了。1973年,苏格兰医生格雷尼姆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伦敦又实施了。当代著名的美国作家欧文·华莱士的《圣床》就是这样一部记实体的小说,该书曾在1987年《纽约时报》上被列为全美1986年十大畅销书之一。
徐:现在中国人对性的要求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了,对夫妻间的性满足要求也不再成为不道德的事,这些观念恐惧也是从那时的“性革命”中得来的好处。
刘:是的,可以说“性革命”加强了夫妻关系的调适,提高了性生活的质量。西方的一些人认为,所谓“性革命”,就是要使人们得到性满足,而这种性满足首先要在婚姻关系的范围内获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封闭式的婚姻为开放式的婚姻所取代,旧的婚姻模式被新的婚姻模式所取代。
徐:什么是新的婚姻模式?
刘:旧的婚姻模式是指夫妻双方在一起过日子,生孩子,强调对社会的义务,爱情不一定那么重要,性生活和谐更显得无关紧要。这种婚姻缺乏调适,缺乏弹性,缺乏变化,无条件地强调“天长地久”。而新的婚姻模式则有许多变化,其中一个重要之点是对夫妻性生活寄予很高的期望,人们把性生活看成是夫妻生活、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没有性生活,家庭就是空虚的,如果性生活不谐调,夫妻关系就可以不必存在。所以,夫妻双方要掌握性生理知识,相互配合,掌握性技巧,使双方都能获得极大的性满足;只好双方能获得最大的性快乐,一切方式、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在“性革命”过程中,许多人因为重视了夫妻性生活的和谐,从而提高了婚姻生活的质量。
徐:从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来看,欧美人是不是过分地强调了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
刘:是的,有些夫妻过于强调了性,而忽视了思想感情的交流,从而又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
徐:在刚才您说的夫妻间的谐调来看,要取得性生活的和谐,妇女原来的“性角色”恐惧是要改变了。
刘:对,由于此前进行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妇女对自己在生活中和夫妻性生活中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性革命”推动了这一角色的转变。
徐:在我们谈女子的贞洁观时谈到,古代人对女子的贞洁的要求出自保证后代的纯洁性需要,自从避孕手段的实施后,使生殖与性分离了出来,但真正从观念上彻底转变的还是从“性革命”开始的吧!
刘:人类的性行为有快乐、健康和生殖三大功能,但是长期以来把性作为生殖的唯一功能,近200年来,这种限制被逐渐打破,18世纪初英国的康顿发明了阴茎套,1838年发明阴道隔膜,1877年英国宣布避孕合法,到了20世纪前期,避孕法逐渐推广,50年代又发明了口服避孕药、节育环和结扎术,由此,性和生殖分离了出来,人们对没有后顾之忧了,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追求性的欢乐。这种情况既推动了“性革命”的产生,又使“性革命”进入安全、科学的轨道。两者有密切的联系。不过,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多,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构成也越来越低,婚外性行为也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于是性放纵与性泛滥猖獗一时。
徐:西方对性的控制主要来自宗教,在“性革命”的时期,宗教是怎么看待这场革命的?
刘:1977年,一群天主教的神学家提出了一份在西方教会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声明,他们不顾梵蒂冈在1976年重新对“婚姻外各种性关系“的责难与禁令,竟然大胆地提出了八项主张:一是婚外性行为如果真的“有创意”而且“圆满”,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二是不应该将离婚者或丧偶者视为“无性的人”;三是同性恋者的稳定友谊比禁欲要来得好;四是结扎术已被视为一种合法的节育方法;五是只有会产生严重心理障碍的不良自慰才是有问题;六是只有当事人有畅通的异性恋的发泄渠道而还要去搞兽奸者,才应被视为病态;七是大多数的色情刊物对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说仍是“中性的”或“无关道德”的,未必那么危险;八是任何形式的性行为只要是“自在的、让对方满意的、忠实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愉悦的”,就应是符合道德的行为。
他们认为,在禁欲主义国家,“贞洁的力量”只是对肉欲的迫害的必然补充,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能大胆地而且审慎地采纳一个彻底的性自由制度,那么确信,与桃色事件有关的个人和社会危险将会大量减少,性心理疾病将会消失。
徐:这恐怕也只是少数宗教者的声明,因为很明显,这份声明已经走向极端,已经无视性的完全自由将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刘:是的,它地过分追求导致了享乐主义、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主义和感官主义,这对人们的人生观是十分有害的。它实际上就是纵欲主义。
徐:前段时间,我看了《海特性学报告》,她虽然是站在妇女的角度来看性,但她似乎是对“性革命”进行批判最多也是最有力的性学家。
刘:是的,在西方的性学家中,较早对“性革命”进行批判的是海特。她指出,“性革命”虽然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使男子的兽性、敌意和剥削意识获得了解放。她认为,“性革命”是隐藏在虚伪的激进表象和伪现代意识背后的所谓革命,它是男性中心文化的产物,其中心宗旨仍然是男性的价值,女人的传统角色不但始终没有改变,还使女人失去了在性行为中说“不”的权利,使女人从私有财产就成了更容易得到的公共财产,所以,从这场革命中获益最多的是男人。
徐:这显然是女人的怨声,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据报道,换妻活动首先都是丈夫提出,但妻子后来也尝到了“甜头”,对此有些留恋忘返了。
刘:海特是完全站在女人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性革命”的,可是也不能截然分开认为男人是“性革命”的受益者,占了便宜,女人成了受害者。从根本上说,“性革命”的脱轨,无论男人和女人都是一种损害、歧途和灾难。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社会历史学者布伦格认为,
“性革命”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时代的悲剧”,她提醒世人,“性自由”决不等于性放纵,美国少女不理解这一点,20岁不到就急于“享受”肉体的“性自由”,整个社会都尝到了理想败坏的苦果。在西方社会,像布伦格这样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了。到90年代,向来以“自由”著称的美国也要向“性革命”低头了,开始“回归”了。美国《新闻周刊》在9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项民意调查指出,认为发生婚外性行为是羞耻的占到了62%,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仍是和固定的一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在1992年,83%的人只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或没有性伴侣。在1969年,只有17%的男子和29%的女人认为“没有爱的性是不快乐或无法接受的”,而到了1983年,认同这一观点的男子和女子分别增加到29%和44%。在问及“你想从伴侣关系中得到什么”时,回答是“爱”的占了53%,而回答是“性”的只占1%。
不仅美国人是这样认为的,整个欧洲人也在改革,“性革命”已经宣告结束。“只有爱情能使生活有意义。”这是80年代以来多数前联邦德国公民的看法。在法国,同居者从1984年开始,每年递减2%,到1989年已减少了9.9%。英国青年对性的态度也比过去严肃得多了。在日本,有80%以上的人反对婚前同居和未婚先孕。
徐:“性革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这个过客却给人类不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也留下了许多教训和反思,它对其它各民族和未来的人类必将是有益的。
为它产生于美国70年代的“性革命”,现在只不过是余波而已。一提起美国,我们对它的感觉便是自由,尤其是性自由。从那些四海同时播放的好莱坞影片中,我们总是能得出一个结论:漂亮的女主人公在认识一个同样性感的男人五分钟后,就可以上床;而且他们的性欲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强,他们的性伴侣难以计数,他们的孩子很早时就在学校里发生无数的性行为,他们的家庭总是被性困扰着,等等,总之,给我们这个传统保守的民族一个深刻的印象,美国就是一个放纵的民族。他们的生活被我们说成是腐朽的,他们的行为是自由化,我们总是在内心深处一边接纳它,又一边提防着它,生怕它那床上的功夫毒害了我们的民族。现在看起来,它一方面可能是宣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有历史原因的,也就是说,美国人有着“性革命”的历史。也许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就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东西。从上面这个旧闻中,我们就可以窥见美国人的“性革命”是怎么回事了。
刘:“性革命”是在美国发生,但它迅速在整个西方社会流行。中国人对它的了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那时已经到了“性革命”的尾声。“性革命”爆发于60年代的西方社会,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人们对它的评价,一直是褒贬不一。王溢嘉在《性·文明与荒谬》一书里对它进行了一番折中的总结:“它‘复古’的成分可能要大于‘革新’,从历史与进化的宏观格局来看,‘穿衣服’与‘禁欲’才是‘革命’,‘脱衣服’与‘纵欲’实在是‘复古’。从观念与行为的认知结构来看,‘性革命’的内涵都是早就‘存在’于个人隐密而恣纵的性幻想中,或者其他文化、其他阶级的日常生活之中,它的现身只是一种公开而普遍的‘实践’”
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从“性革命”对维多利亚时代禁欲主义的彻底扫荡来看,这也可以算是一场革命;如果从“性革命”以后脱轨,走向裸体、纵欲、滥交来看,这的确是“复古”到野蛮时代去了,那不是革命,是倒退。不过,无论怎么说,“性革命”总是人类性发展史中否定之否定的长链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还是值得分析的。
徐:正如上面消息中所说的,“性革命”时代,参加这一运动的大都是些个性反叛的青年,而且他们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出身也比较富有。可能就像现在我们国家出现的“七十后”这一代吧,他们自称为小资。那时,美国的青年主要干了些什么?
刘:由于他们不满足于传统的小家庭生活方式,反对对性的压抑和禁锢,对传统的两性关系形式表示了极大的反抗。他们单纯强调要尽情地享受性的快乐,过早地发生婚前性行为,甚至公开同居,视结合与离异为儿戏。有些青年还聚居在一起,组成“大家庭”,过群婚乱交的生活;此外还出现了许多婚姻形式,如同性恋婚姻、合同婚姻、临时婚姻、家庭群等。
徐:您前面说过,这是历史否定之否定中的一链,也就是“性革命”在您看来有着历史渊源。
刘:是的,它不是偶然产物,而是一种必然。这得上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那种肯定现世人生、追求人世欢乐的思想:提倡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而这些思想一旦和性联系起来,就成了对“性自由”的追求。
但是欧洲清教运动的兴起和维多利亚主义的广泛流行,使人文主义的光辉暗淡了下来,社会思想又从开放走向了保守和禁锢。到了20世纪,各种思想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发展,重新又唤起了失落的人文主义,因而也唤醒了性。
徐:这应该是思想根源。欧洲文艺复兴如果说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纵欲主义的复兴的话,这次性解放应该走得更远,它试图与原始社会的性达成一致。19世纪末科学主义和进化论、考古学、人类学的兴起,使人类不仅对宗教思想进行了更大的打击与报复,还使人类睁开了眼睛,发现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从亚当和夏娃开始,而要更早,对家庭婚姻制度的研究也使人类对两性关系有了重新认识。这一切使60年代的“性革命”带上了“野蛮”的色彩,实际上这正是人们的学说影响的。如果没有“原始群婚说”,如果没有对偶婚的发现,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不否定一夫一妻制(他们预言一夫一妻制将随国家、法律等的消亡而消亡),那么,那些群婚乱交的行为就不会有理论基础。可以说,“性革命”是这些学说的副产品。
刘:这只是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的,关于性的理论才是“性革命”真正的理论基础。19世纪末兴起了现代性科学,先是弗洛伊德从本能生物学上认为,存在于无意识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是支配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尽管他遭到了很多批评,但人们对性的真正关注和重视,却是从他开始的。后来,霭理士一再地强调:“性是自然而令人喜欢的”,“性欲是卑下邪恶的观念乃是宇宙中的一大荒谬,就好像疯子认为他的食欲是邪恶而拒绝进食一样”。在两位先驱的影响下,后世学者极力地鼓吹性欲应该怎么自由,
这些都从根本上引导了人们的性观念。而40年代和50年代公布的两个金西调查报告对“性革命”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人们读了金西教授的报告后得出一个结论:既然人们的性生活实际上竟是如此,我为什么还要抱着那陈旧的一套不放呢?
徐:我们中国人对性心理学的泰斗弗洛伊德知道的已经很多了,但对另一个泰斗霭理士以及现代性学先驱金西并不了解,请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刘:霭理士是英国的性心理学家、作家、文学评论家,他出生的时候正是维多利亚性保守主义的全盛时期,他本人有着严重的性困扰,深受其害。他当过教师,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并挂牌行过医,但不久就专心于文学写作评论和性研究。他不是从某个学科领域单独地研究性问题,而是从民族学、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诸领域综合论述性的问题。他的著作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性心理学》和《天才与遗传》等。
在谈金西教授之前,我们必须还得说说他前后的几个在人类性学方面有着重要贡献的人。
在历史上最勇敢地站出来进行人体性实验的人是美国科学家华生。因为在此以前,人们对性的认识一直停留在社会科学方面,充满了臆测、迷信和无知,还有恐惧。要真正理解人类的性行为,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性反应的客观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例如男人和女人的性欲究竟是不是相同的,女性性反应高潮是否可以截然分出“阴道高潮”和“阴蒂高潮”,自慰行为究竟对人体有没有害处,等等。在那时,他进行的性反应实验研究,是无人和他合作的,妻子更是持反对态度,他只好偷偷地和女秘书在实验室里进行,积累了大量实验资料,最后却被妻子发现付之一炬,并被法院判决他是“坏行为的专家”。他也被大学辞退,做了一个广告公司的小职员,后半生碌碌无为。但他的心理学专著,至今仍被人学习、引用。
完成华生未竟事业的是四十多年后的玛斯特斯和约翰逊夫妇,这时候,“性革命”已经开始了。在11年中,他们所观察的模拟性交和实际性交实验达1万次,其中男性2500次,女性7500次。他们把大量的实验数据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于1966年出版了第一部专部《人类性反应》,轰动了整个西方社会,成为现代性科学的经典著作。他们的研究,革新了人们对性反应的认识,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具有划时代影响的金西教授的调查。美国人亚弗雷德·金西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26岁就成为印第安那大学生物学教授,在1938年因为这所大学的女联会学生代表要求学校为那些已经订婚、结婚或准备结婚的学生开设有关“人类性学”的课程,他就成了这门课的教师。在他备课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学科缺乏具有科学依据的统计资料,无法回答学生的提问。于是,他放弃了先前对昆虫有研究,开始了有关性的调查。在整整10间,他和他的同事们对17000人进行了调查,于1948年出版了《金西报告》的男性篇《人类男性性行为》,人们终于知道,有90%以上的男性有过自慰的经验,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男性承认从青春期开始至少有过一次与其他男性的性经验。1953年,女性篇《人类女性性行为》出版,人们突然发现,有一半的女子在婚前有过性行为,25%的女性承认自己有婚外性行为。
金西研究的原意是想打破社会上对性行为保持缄默的维多利亚时代式的旧观念,可是他的调查报告一出,随之而来的性行为的自由和性方面的公开讨论与研究就一发不可收拾。那些数据大大动摇了常人的道德观念,突然间,性方面的话题不再限于卖淫、性病、节育和弗洛伊德理论等等,而进入了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同性恋、性变态等过去避而不谈的禁区。这个报告的影响远不至如此,他使美国的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的那一套性的道理规范被认为是虚伪的,站不住脚了。所以完全可以说,金西报告在理论上直接推动了美国60年代开始发生的“性革命”。
西方社会对性学的研究从金西以后就非常热闹了,似乎每10年就出现一两位代表人物:就50年代来说,是金西的调查;就60年代来说,是玛斯特斯和约翰逊;就70年代来说,是莎丽·海特;就80年代来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劳曼、马可和迈克斯等人的调查。
徐:这些调查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在方法论上改变了以往的研究,还给性在统计学上定位了。这种定位究竟有没有道理,我倒总是怀疑,因为不一定人人都这样就这认为这是好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不过,它毕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足以说明它是可以信赖的。
刘:前面所说的只是观念上的原因,在经济、政治方面也有原因。如前面所说,“性革命”的主要参加者大都是中产阶级,他们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而“性”也想当然地成为消费的对象。有的学者还把美国汽车业的迅猛发展也看成“性革命”的推动者,因为它可以在几分钟之内让那些年轻人逃离道德的包围圈,而进入另一个相对陌生、自由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至于政治上的原因,很多学者主要把它归于两次世界大战。许多人庆幸战争的灾难已经过去,生命实在太短暂了,还不如及时行乐的好。
徐:这让我想起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写的那首著名的诗《嚎叫》,和另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等待戈多》、《在路上》,它们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那时的美国青年是何等地空虚、无聊而又绝望,绝望到了要嚎叫。
而这空虚和绝望又使我想起西方一个哲人大叫“人死了”,这是继尼采的“上帝死了”之后对人类价值,准确一些说是人文主义的绝望。他们再也找不到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于是行为主义就成为青年人推崇的重要方式。而行为主义在根本上说,也是无事无补的,因为它无法说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行为本身似乎也死了。这就是说,这个世界死了。这是多么地可怕!由此我想说的是,既然西方世界的精神已经倒了,他们所奉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矛盾与倒退,而我们的青年却还是觉得人家的好,要不顾一切地模仿,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的很多学者,如果一旦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会对人说:“你看看人家西方是怎么怎么地”,西方成了唯一的准则。我希望“性革命”不要也被我们的社会学家和性学家毫无取舍地推行到中国来。
刘:前面我们似乎已经谈过,我觉得中国是不可能爆发“性革命”的,因为我们古老的文化在制约着性。
徐:但愿如此。除了前面说的原因外,还有哪些原因?
刘:妇女解放运动也是“性革命”的兴奋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阶级的融合--人口从乡间涌向城市,人际空间渐趋紧密,职业妇女地位提升,使得传统的父权制逐渐崩溃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男子上了战场,女子取代他们的工作,使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而取得独立。在这种运动中,有不少妇女产生了争取性自由的勇气,妇女在性方面的开放和主动也成为“性革命”的重要内容。
除了这些原因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20世纪性之所以非常开放的重要原因,就是口服药和避孕套的使用。这是科学带来的。科学说,你们大胆地进行性交吧,只要你们不忘记我的发明。人们也这样做了,而且发现它完全实现了另一场革命,那就是生殖与性活动可以分离。
徐:既然人们对“性革命”有褒有贬,也就是说它既有合理发展的一面,又有可恶的一面,那么,如何来认识它呢?也就是说它如何在真理与荒谬间徘徊的?
刘:前面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点,这也是首要的一点,就是性学家对性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对性的神秘感和负罪感,使人类得到了一定的解脱。同时,也使人们开始重视性科学研究和性教育的普及。在这些研究中,除了金西的调查外,尤其要提的是玛斯特斯夫妇的实验,他们的理论可以说奠定了性科学的基础。
徐:我们都知道人类性反应的四周期理论是他们提出来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得出了哪些惊人的结论?
刘:他们第一次指出,男女性反应极其相似,并不是女性比男性迟钝或相差甚大,并纠正了弗洛伊德提出的女子性反应高潮分为“阴道高潮”和“阴蒂高潮”两个阶段并极力贬低“阴蒂高潮”从而引起很多不良后果的错误说法;他们发现男性阴茎的大小与性快感并无必然关联,发现女性的阴蒂和男性的阴茎并非类同的器官,并发现阴道润滑液的产生是性兴奋时阴道壁的一种“发汗”,而不属于腺体分泌物;他们还发现决定男女生理特征的同一性激素并不是其绝对数量,而是其比值;他们纠正了手淫对人身体有害的错误说法,明确了勃起中枢是在脊髓的末端部位,等等。他们的发现对如何促进性健康,保持和谐的夫妻性生活,以及有效地进行性治疗,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创造了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见效而且总疗效在80%以上的各种性功能障碍的新治疗方法。
徐:说到这里,我想起在我刚刚毕业时看过的一本《圣床》,当时被认为是黄色书籍查禁了。
刘:玛斯特斯夫妇对阴萎的治疗提出用“双性疗法”,而且这也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对多数患者是奏效的,但对一些夫妻不怎么合适,特别是有些男子是未婚的,就不可能用夫妻的方法来治疗,所以他们大胆地使用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女性担任“代配偶”进行治疗。但是这一做法与社会道德发生严重的冲突,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卖淫”,所以这种方法到1970年停止了。1973年,苏格兰医生格雷尼姆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伦敦又实施了。当代著名的美国作家欧文·华莱士的《圣床》就是这样一部记实体的小说,该书曾在1987年《纽约时报》上被列为全美1986年十大畅销书之一。
徐:现在中国人对性的要求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了,对夫妻间的性满足要求也不再成为不道德的事,这些观念恐惧也是从那时的“性革命”中得来的好处。
刘:是的,可以说“性革命”加强了夫妻关系的调适,提高了性生活的质量。西方的一些人认为,所谓“性革命”,就是要使人们得到性满足,而这种性满足首先要在婚姻关系的范围内获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封闭式的婚姻为开放式的婚姻所取代,旧的婚姻模式被新的婚姻模式所取代。
徐:什么是新的婚姻模式?
刘:旧的婚姻模式是指夫妻双方在一起过日子,生孩子,强调对社会的义务,爱情不一定那么重要,性生活和谐更显得无关紧要。这种婚姻缺乏调适,缺乏弹性,缺乏变化,无条件地强调“天长地久”。而新的婚姻模式则有许多变化,其中一个重要之点是对夫妻性生活寄予很高的期望,人们把性生活看成是夫妻生活、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没有性生活,家庭就是空虚的,如果性生活不谐调,夫妻关系就可以不必存在。所以,夫妻双方要掌握性生理知识,相互配合,掌握性技巧,使双方都能获得极大的性满足;只好双方能获得最大的性快乐,一切方式、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在“性革命”过程中,许多人因为重视了夫妻性生活的和谐,从而提高了婚姻生活的质量。
徐:从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来看,欧美人是不是过分地强调了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
刘:是的,有些夫妻过于强调了性,而忽视了思想感情的交流,从而又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
徐:在刚才您说的夫妻间的谐调来看,要取得性生活的和谐,妇女原来的“性角色”恐惧是要改变了。
刘:对,由于此前进行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妇女对自己在生活中和夫妻性生活中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性革命”推动了这一角色的转变。
徐:在我们谈女子的贞洁观时谈到,古代人对女子的贞洁的要求出自保证后代的纯洁性需要,自从避孕手段的实施后,使生殖与性分离了出来,但真正从观念上彻底转变的还是从“性革命”开始的吧!
刘:人类的性行为有快乐、健康和生殖三大功能,但是长期以来把性作为生殖的唯一功能,近200年来,这种限制被逐渐打破,18世纪初英国的康顿发明了阴茎套,1838年发明阴道隔膜,1877年英国宣布避孕合法,到了20世纪前期,避孕法逐渐推广,50年代又发明了口服避孕药、节育环和结扎术,由此,性和生殖分离了出来,人们对没有后顾之忧了,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追求性的欢乐。这种情况既推动了“性革命”的产生,又使“性革命”进入安全、科学的轨道。两者有密切的联系。不过,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多,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构成也越来越低,婚外性行为也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于是性放纵与性泛滥猖獗一时。
徐:西方对性的控制主要来自宗教,在“性革命”的时期,宗教是怎么看待这场革命的?
刘:1977年,一群天主教的神学家提出了一份在西方教会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声明,他们不顾梵蒂冈在1976年重新对“婚姻外各种性关系“的责难与禁令,竟然大胆地提出了八项主张:一是婚外性行为如果真的“有创意”而且“圆满”,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二是不应该将离婚者或丧偶者视为“无性的人”;三是同性恋者的稳定友谊比禁欲要来得好;四是结扎术已被视为一种合法的节育方法;五是只有会产生严重心理障碍的不良自慰才是有问题;六是只有当事人有畅通的异性恋的发泄渠道而还要去搞兽奸者,才应被视为病态;七是大多数的色情刊物对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说仍是“中性的”或“无关道德”的,未必那么危险;八是任何形式的性行为只要是“自在的、让对方满意的、忠实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愉悦的”,就应是符合道德的行为。
他们认为,在禁欲主义国家,“贞洁的力量”只是对肉欲的迫害的必然补充,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能大胆地而且审慎地采纳一个彻底的性自由制度,那么确信,与桃色事件有关的个人和社会危险将会大量减少,性心理疾病将会消失。
徐:这恐怕也只是少数宗教者的声明,因为很明显,这份声明已经走向极端,已经无视性的完全自由将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刘:是的,它地过分追求导致了享乐主义、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主义和感官主义,这对人们的人生观是十分有害的。它实际上就是纵欲主义。
徐:前段时间,我看了《海特性学报告》,她虽然是站在妇女的角度来看性,但她似乎是对“性革命”进行批判最多也是最有力的性学家。
刘:是的,在西方的性学家中,较早对“性革命”进行批判的是海特。她指出,“性革命”虽然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使男子的兽性、敌意和剥削意识获得了解放。她认为,“性革命”是隐藏在虚伪的激进表象和伪现代意识背后的所谓革命,它是男性中心文化的产物,其中心宗旨仍然是男性的价值,女人的传统角色不但始终没有改变,还使女人失去了在性行为中说“不”的权利,使女人从私有财产就成了更容易得到的公共财产,所以,从这场革命中获益最多的是男人。
徐:这显然是女人的怨声,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据报道,换妻活动首先都是丈夫提出,但妻子后来也尝到了“甜头”,对此有些留恋忘返了。
刘:海特是完全站在女人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性革命”的,可是也不能截然分开认为男人是“性革命”的受益者,占了便宜,女人成了受害者。从根本上说,“性革命”的脱轨,无论男人和女人都是一种损害、歧途和灾难。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社会历史学者布伦格认为,
“性革命”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时代的悲剧”,她提醒世人,“性自由”决不等于性放纵,美国少女不理解这一点,20岁不到就急于“享受”肉体的“性自由”,整个社会都尝到了理想败坏的苦果。在西方社会,像布伦格这样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了。到90年代,向来以“自由”著称的美国也要向“性革命”低头了,开始“回归”了。美国《新闻周刊》在9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项民意调查指出,认为发生婚外性行为是羞耻的占到了62%,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仍是和固定的一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在1992年,83%的人只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或没有性伴侣。在1969年,只有17%的男子和29%的女人认为“没有爱的性是不快乐或无法接受的”,而到了1983年,认同这一观点的男子和女子分别增加到29%和44%。在问及“你想从伴侣关系中得到什么”时,回答是“爱”的占了53%,而回答是“性”的只占1%。
不仅美国人是这样认为的,整个欧洲人也在改革,“性革命”已经宣告结束。“只有爱情能使生活有意义。”这是80年代以来多数前联邦德国公民的看法。在法国,同居者从1984年开始,每年递减2%,到1989年已减少了9.9%。英国青年对性的态度也比过去严肃得多了。在日本,有80%以上的人反对婚前同居和未婚先孕。
徐:“性革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这个过客却给人类不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也留下了许多教训和反思,它对其它各民族和未来的人类必将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