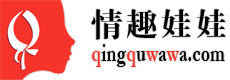从11月17日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连续播出了记者暗访江苏南部村庄输液器、注射器造假情况的报道,引起强烈反响。江苏省政府在22日下午召开打假工作紧急会议,会上播放了新闻纵横节目的录音,并据此部署了全省的打假工作。应该说江苏打假初战告捷,新闻纵横的报道也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是,记者在这次打假行动报道中的困惑和思考却没有停止。为什么假冒产品屡禁不绝?我们是不是要一年又一年重复没完没了的打假故事?近日,采访此事的两位记者来到了中央台《新闻背景》演播室,为听众介绍了打假新闻背后的新闻。来到演播室的还有《新闻背景》节目的记者杜昌华。
主持人:通过你们对假冒伪劣现象报道之后,是不是自己也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呢?
打假记者:以前只听说打假、制假,但从没有跟他们接触过,也没有像这次与他们接触得这么近,确实是触目惊心。
主持人:到底触目惊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给我们描述描述。
打假记者:当时去采访在苏南江阴和武进这两个县级市交界的地方。根据得到的线索,这个地方制造假冒伪劣一次性注射器非常猖獗。我们去看以后确实如此,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制假现象。我们去了江阴四河口镇野山沟村,到这个村子以后,说要买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村民不卖给我们,因为我们两个是外地口音。我们说我们是东北来的,他们说你要拿出身份证来证明你是东北的,我们就可以卖给你。我们当然没有东北的身份证,所以就不行。我们在村子里走了一圈,看见几个农妇抱着大包大包输液器、注射器的成品,在村子的道路上走来走去,路上全是掉的一次性的注射器,非常明目张胆,让我们触目惊心。这个东西应该是严令禁止的,但是在村子里处于一种半公开的状态。作为一个外地人,作为一个陌生人,你想去买他的假货,这些制假者有很强的防范意识,警惕性非常高,他不会卖给你。
主持人:你们在跟姚老板接触的过程中,是不是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打消他的警惕性?
打假记者:是这样的,姚老板一开始也怀疑我们,幸亏我们是东北口音,我们说是从东北来的。一开始姚老板非常谨慎,问我们从哪里来、要看我们的身份证、要我们电话,我们都没有。在谈价钱的时候,我们装作对这个行情比较了解,谈的时候还比较内行。姚老板他确实是财迷心窍……
主持人:你们离开村庄的时候,姚老板的母亲要留你们吃饭是吗?
打假记者:从姚老板的家庭气氛来看,感觉他不是一个特别坏的人。
打假记者:但是从他的自我介绍了解到,他始终没有做正当的生意。最早的时候他是做假烟的,后来从事假冒伪劣的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到现在为止已经有8年了。
杜昌华:他清不清楚做这件事是很缺德的、是危害社会的?
打假记者:要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制假、售假,这不可能。他从事了这个行业已经8年了,已经有很强的专业知识了,但是我感觉他的法律意识并不是很强。他只顾去赚钱了,他除了在制假这方面恶劣以外,他的家庭是很融洽、和谐的。从这可以感觉出这些农民制假者,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害者。我举一个例子,在浙江东阳有一些农民,把回收回来的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洗了以后,重新包装,再卖出去。这比姚老板的制假更加恶劣,这个农民制假者自己没有干多长时间,就传染上肝炎了,他本身是危害他人的人,但自己又是受害人。从这里可以感到,一方面他是受害于自己,另一方面是受害于我们的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这么多年打假,如果一开始打击得特别严厉,一下子打灭了的话,也可能姚老板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打假不力、执法不严使姚老板存在一个侥幸的心理,觉得这种生意能做的下去,从这方面来说他也是个受害者。
杜昌华:我昨天就这次打假的一些事,采访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的郝和平司长,他也提到在基层很多人,根本没有把造假当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郝司长:有的部门对打击制售假劣一次性医疗器械的认识,还没有认清,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人认为打击制售一次性医疗器械算不了什么事,没有造成事实,金额也不够,一万、两万不够刑事审查的限度额度,抓人你怎么抓?
打假记者:是这样的,我列举一个例子,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毛局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这次我们所发现的姚老板制假,江苏省药品管理监督局早就发现这个地方线索,早就把它列为排查的重点了,已经通知无锡地区江阴市,但江阴市的各级政府始终也没有查到这个村子里有制假的现象,这就是基层部门排查力度不够。我们作为外地人,去了以后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些制假者。
主持人:尽管有很多部门都应该打假,应该从行动上尽快贯彻执行,实际大家都在相互推诿。在你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抓到基本事实、基本线索,要进村的时候,当地的有关部门执法者都云集在村口,当时决定由谁来指挥,谁先进,谁后进,谁也不愿意指挥,最后决定让你们两位记者来指挥,当时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呢?
打假记者: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在南京中山宾馆我们开了一个会,有江苏省公安厅、江苏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样一些部门,包括一些新闻单位,商量谁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谁是打假主体,在这里发生了一些分歧。公安方面同志认为自己是配合,既然是打击假冒伪劣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应该是以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主体;药监局认为我们已经知道是制假者了,他已经触犯法律了,要抓人,涉及具体搜查了,应该是公安来做主体,我们配合。最后大家觉得国家药监局是国家来的,是不是你应该来做总指挥,可是国家药监局的同志说,对于当地的具体事情都不了解,包括地形什么的都不熟,做总指挥是不是不妥。这个时候大家感觉,既然是你们新闻单位提供的新闻线索,你们又要报道,干脆听你们的,由你们做总指挥。我们感到非常尴尬。
杜昌华:我在采访郝局长的时候也提到,打假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一件事情,光靠药品监督管理局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听一听采访录音。
郝局长:打假各个部门要联合行动,国务院三令五申地讲要协同作战,要去抄这些制假窝点,要去抓这些案犯,你公安部门不出面不行,当地工商部门不出面不行,技术监督部门不出面不行。还有当地的政府,特别是江阴市政府,不积极配合也不行。这些部门是不是认为打击制售一次性医疗注射器、输液器应该作为社会公害彻底铲除?我看不一定有这样的认识,他对我们布置下去的工作,对省领导的批示执行起来会打折扣。
主持人:郝司长说要共同关注,恰恰是共同关注,让大家也都不承认自己是打假的主体,事情总也得不到解决。
打假记者:说到共同关注,我举一个例子。在查案的时候,姚老板跑了,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国家药监局和省公安厅治安处的朱处长俩人在车上谈论打假谁是配合,谁是主体。他们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况:作为药监局我去执法去了,我知道这些都是假货,这里有生产假货的机器,但是制假者把门锁上了,我现在进不去,门由谁来踹?药监部门说由公安部门来踹,但是治安处的说,我们要有搜查证才能踹,回去还得申请搜查证,这样一来二去人早就跑了。
打假记者:不能不说他们没有道理,但是在客观上拖延了打假的时间,这是在打假过程中出现多头管理、互相推诿责任的问题。
在这次报道中我们还知道有些正规企业也和制假者相互勾结起来,他们也参与制假了。这些正规企业在管理方面也存在多头管理,最后也有互相推诿责任的问题。比如说正规的输液器、注射器厂家需要三证,就是企业生产合格证、卫生合格证、市场准入证。生产合格证是国家经贸委下属国家技术监督局发的;卫生许可证是由卫生部门来发的,因为涉及到一些卫生防疫的问题;市场准入证也叫产品注册证,这是药监部门或者是地方的医药部门来发的,这样的企业具备三证,可以说三个部门都应该管理、多头管理。但是,到了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开始互相推诿。在管理的时候,三家都出来管理,该负责任的时候,大家都互相推诿。
主持人:一个正规厂家也造假冒伪劣的东西,这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可思议。